AI 学习写作的 AI:辅助学习,提升写作能力
让 AI 教我写作?或者说,用 AI “辅助”我写作?那感觉……就像请了个枪手,还是个没有灵魂、说话一股翻译腔的塑料枪手。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那些由 AI 生成的、四平八稳、滴水不漏但就是读不下去的“标准答案”式文本。
那不是创作,那是复制粘贴的排列组合。是对文字的亵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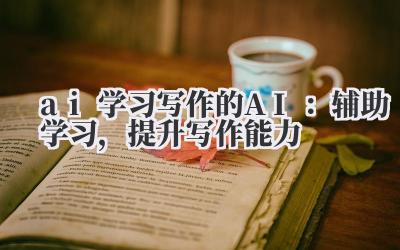
很长一段时间,我把写作 AI 扔在工具箱的角落里,碰都不碰。我觉得,写作这件事,必须是“纯粹”的,是一个人在书房里,对着一方屏幕,一个字一个字地从脑子里、从心里抠出来的过程。痛苦,但神圣。
直到有一次,我被一个项目报告的开头憋得死去活来。那种感觉,写过东西的人都懂——脑子里明明有无数想法,像一锅沸腾的粥,但倒在纸上,就是一坨坨黏连的、毫无形状的浆糊。光标在屏幕左上角,像个心烦的脉搏,一下,一下,一下地跳着,嘲笑着我的词穷。
绝望之际,我鬼使神差地打开了那个 AI 对话框。但我没让它“帮我写一个开头”。我恨透了这种指令,这等同于放弃思考。
我换了一种玩法。
我把我那坨浆糊一样的初稿,那段我自己都嫌弃的、冗长又混乱的文字,直接扔给了它。然后,我下达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指令:
“分析这段文字的弱点。别给我重写,告诉我,它为什么读起来这么烂?”
几秒钟后,它给出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开头,而是一串列表:
- 句子结构单一,连续使用了五个“我们……”开头的长句,造成阅读疲劳。
- 核心观点“效率提升”被淹没在过多的修饰词和无关细节里。建议前置。
- “关键”、“重要”、“核心”等词语在短时间内重复出现,稀释了强调效果。
- 缺乏一个能抓住人眼球的“钩子”。
我盯着那几行字,愣住了。
它……说得对。
它就像一个冷酷无情的外科医生,精准地解剖了我的“病文”,指出了病灶。它没有替我动刀,但它递给了我手术刀,还标出了下刀的位置。
那一刻,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。问题不在 AI,而在我们怎么用它。我们一直把它当成一个自动售货机,投币(指令),取货(文本)。但它真正的潜力,是成为一面镜子,一个放大器,一个不知疲倦的陪练。
从那天起,我彻底改变了和 AI 协作的模式。我的写作过程,不再是一个人的苦修,而是一场双人舞,或者说,一场我和一个虚拟“教练”的对打。
我的第一个玩法,是把它当成“思维的墙壁”。
写初稿时,我会把所有杂乱无章、不加修饰的想法全喷涌出来,就像对着墙壁说话。然后,我把这堆“意识流”扔给 AI,让它帮我“提炼核心论点”和“梳理逻辑框架”。它会像一个最耐心的助理,帮我从一团乱麻里抽出几根清晰的线头。我再拿着这几根线头,去重新编织我的文字。这极大地解决了“万事开头难”的魔咒,让我能快速越过最痛苦的“从0到1”阶段。
然后,更有意思的来了——我把它用作一个“句法可能性的探索器”。
写完一段我自己觉得还凑合,但总感觉有点平淡的文字,我会把它发给 AI,然后下达这样的指令:“用五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和句式,重写上面这段话。要求:一种要像王家卫的电影台词,一种要像科技媒体的快讯,一种要像村上春树的小说,一种要简洁有力,一种要华丽铺陈。”
出来的结果,90%是不能直接用的。有的模仿得很可笑,有的完全失去了原意。但那不重要!重要的是,剩下的10%给了我巨大的启发。它让我看到,原来我习以为常的一个句子,竟然可以有那么多种表达的可能。它会用一个我从没想过的比喻,或者一个意想不到的倒装句,瞬间点亮我的思路。
我不会复制它的句子,但我会“偷”走它的思路。它像一个灵感催化剂,强迫我的大脑跳出固有的舒适区,去探索语言的边疆。这才是真正的辅助学习,它不是给我鱼,而是让我看到了整个海洋的捕鱼方式。
再后来,我甚至用它来锻炼我的“文字肌肉”。
我会故意写一段拗口、啰嗦的话,然后让 AI 去“压缩”和“精炼”,看它如何用最少的字表达同样的意思。反过来,我也会给它一个极简的核心观点,让它“扩写”和“填充细节”,观察它会从哪些角度去丰富血肉。
这个过程,就像健身。我不断地给我的“写作肌肉”增加负重、变换角度,AI 就是那个调整器械、递上毛巾的私教。我的写作能力,不是在被它取代,而是在与它的互动和博弈中,被前所未有地强化了。
当然,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陷阱,就是“懒惰”。是那种“啊,它写的这个句子真不错,直接拿来用吧”的诱惑。一旦你屈服于这种诱惑,你的写作之路也就到头了。你的声音会被它的声音覆盖,你的风格会被它的“平均风格”同化。
所以,使用 AI 辅助写作,最核心的一条戒律就是:永远保留最终的审判权和修改权。
把它当成一个无比强大的、但没有任何个人意志的“副脑”。你可以用它检索信息、对比文本、激发创意、检查语法,但最终的每一个字、每一个标点,都必须经过你自己的大脑和心灵的过滤。你的个人风格、你的情感、你的独特观察,才是文章的灵魂。AI 能提供完美的骨架,但灵魂,只能由你亲手注入。
如今,我不再排斥 AI。它就静静地待在我的工具栏里,像一个沉默的伙伴。当我文思泉涌时,我可以完全不理它;当我思路枯竭时,我会把它叫出来,跟它“聊一聊”,或者更准确地说,是借助它,跟另一个版本的自己聊一聊。
它是一面能照见我思维盲区和语言惰性的镜子。它不是帮我写作的 AI,而是帮助我“学习如何更好地写作”的 AI。
这其中的差别,天壤之别。而这,或许才是我们在这个时代,与 AI 共舞的、最优雅也最有效的姿态。